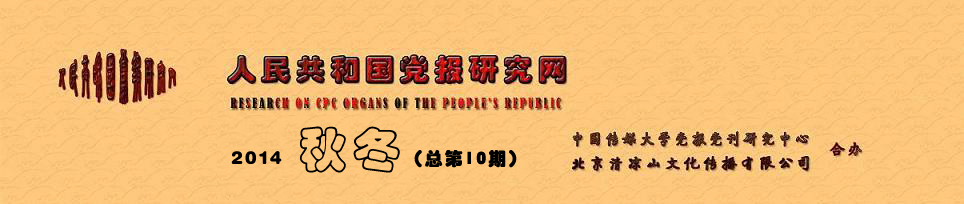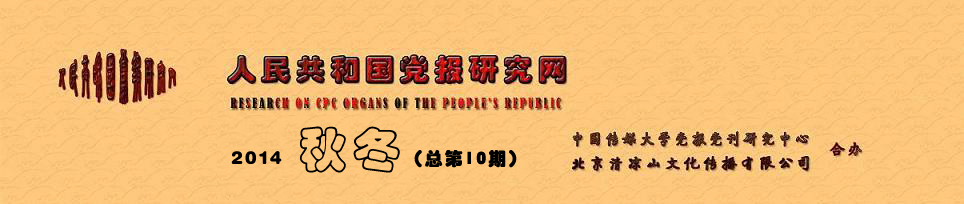|
一、网络谣言成因
谣言并非网络时代的特有产物,但谣言却在网络社会中找到了新的集聚地。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曾说,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 。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谣言也如虎添翼,传播速度更快、内容更驳杂,危害更大。谣言正如进化的生物,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
分析网络谣言的成因首先要从谣言本身开始进行分析,经典的谣言公式: R= I × A由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谣言心理学》中提出,即谣言的流通量= 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 1951 年克洛斯对该公式进行了演进修改: R= I × A × C,即谣言的流通量= 问题的重要性× 证据的暧昧性×听者的批判能力;清华大学胡钰教授提出: 谣言=关注度× 模糊度× 反常度 。从国内外学者对谣言的研究来看,谣言传播与事件的关注度、重要性呈正向相关,而信息和证据的模糊性则负向相关。
网络谣言为何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可以从信息环境、传播源头、传播者心理等几个方面来探讨。
从谣言传播渠道看,网络渠道匿名、发送信息快捷,容易成为谣言萌生地,桑斯坦将互联网称之为谣言滋生的土壤:“互联网时代,散步有关任何人的虚假、具有误导性的谣言都变得十分容易” 。中国社科院在其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指出,微博中出现的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2012年,平均每天就有1.8条谣言被报道,其中六成是与食品、政治、灾难有关的硬谣言(如去年年底,邪教组织“全能神”借助世界末日谣言牟取私利),超过两成是与娱乐相关的软谣言(如明星分手、绯闻等) 。
从“传谣者”即谣言源头来看,造谣者可以分为刻意造谣和无意生谣,刻意造谣者有的为了泄私愤,有的是靠炒作赢取知名度从而从中获益的个人和组织,前者如傅学胜,后者如网络推手“立二拆四”和秦火火、周禄宝等,他们靠造谣泄愤或牟利。如轰动一时的中石化“非洲牛郎门”事件,经查则是造谣者傅学胜因参与中石化招标项目失败为泄私愤而精心策划、恶意编造,而在网上造成轩然大波。针对中石化的《俄罗斯艳女门续集:中石化再曝非洲牛郎门》的造谣诽谤网帖,称“中标的公司利用‘非洲牛郎’对中石化负责招标工作的一名女处长实施性贿赂,才得以中标并获利40万美金”。为达到“轰动效应”,傅还专门花数千元雇佣了网络水军进行转载顶贴、恶意炒作。该网帖迅速成为网络热帖,三天内百度搜索相关信息达11万余条。“7?23动车事故外籍遇难旅客获赔2亿元”“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干爹花888万元包机让嫩模去看伦敦奥运”都被证实为一系列被策划的无中生有的谣言。无意生谣者也选择性接收这些被策划的假信息或断章取义,成为谣言信息的催化剂。
从网民传谣心理来看,除刻意造谣外,无意生谣和造谣者的心理主要可以归结为减少焦虑,传谣者因焦虑或恐慌将谣言当做发泄手段,当众多人都在谈论某件事情本身,而真相缺席,个体出于强烈担忧和对未来走向不确定,将猜测,遐想,臆想当成传播内容,在网络上汇聚一处就成了集体宣泄。如果谣言成真,因为涉及众多的人,就消除了之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的孤独和无助,如果谣言是假,也在充当谈资的同时与公众分担风险,减少了焦虑,因为坏消息在紧张不安时也是一种确定性。
其次从传播学理论来看,谣言源自信息失衡,媒体通常只想告知他们想告知的,而民众只想获知他们想获知的,这就形成了信息格差。谣言通常选择从信息格差的罅隙中发芽,某件与公众联系最密切的物体或话语常成为谣言流行的引爆点,而网络通常成为谣言成长沃土。媒体向公众提供的通常是放大或缩小的信息,如果是负面信息, 公众通常认为自己接触到的都是政府提供给媒体的“被缩小”的信息,于是就产生了媒体和政府越是辟谣,民众越不相信的“塔西佗陷阱” ,这种恶性循环不仅直接导致辟谣失效,也损伤了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双输”。
二、网络谣言的独特性和偏好性
从传播内容来看,为何有的内容成为谣言,为何有的内容却很少被传播,即在网上被制造和病毒式传播的谣言话题往往带有倾向性,这与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有选择的接受、相信、传播信息有关。即网络谣言有其独特性和偏向性。
第一,真实信息缺位和权威信息缺席的事件,尤其是跟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件,如食品安全、病情疫情、非正常死亡事件等,如2012年网络十大谣言中,此类占比50%,分别为“速生鸡”“打针西瓜”“江苏射阳挂号门”“周克华未死系列谣言” “交通违章元旦后处理按新规”。
由于真实、权威的信息缺失或已经发布的信息不完整,被截取的支离破碎,容易成为谣言。“德国心理学家蔡加尼克发现,人们对尚未做完的事情,比已做完的事情记忆更深刻” 。信息不全的公共事件就像还没有做完的事情,会长时间占据人们的关注点。不久前北京京温商城发生的女子坠亡事件,官方迟迟不公布真实原因,人们出于好奇,才会妄加猜测。在传播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对不完整、不确定的内容做出“合理化”补充,导致信息畸变,被更多人当成“事实”。
第二,有争议的热点和话题,尤其是挑战公众“三情”底线的三俗话题和热点。如被捕的网络推手“立二拆四”曾总结话题炒作理论,“副区长贪污20多亿、包养10多名情妇”,“中石化女处长接受‘非洲牛郎’性贿赂”等重口味的话题更容易吸引网民眼球,这些耸人听闻、极具杀伤力的谣言如病毒一样呈几何倍数在网络社会中繁衍扩散。“硬广不如软文,软文不如新闻,新闻不如八卦,八卦不如门,门不如假新闻,假新闻不如违背人伦……” ,这些网络推手以情绪、情感、情欲的“三情理念”挑战人们的心理底线,利用部分网民的不良趣味炮制热点事件、产生“眼球效应”。
第三,以诋毁央企人员或社会正统人物为主的话题。如被拘留的网络推手秦火火,攻击张海迪入日本籍,2 0 1 1 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后,秦火火开始了第一次造谣,谎称动车事故外籍死者获赔两亿,先后造谣传谣3000余条,网友称其“谣翻中国”。
傅学胜则像导演大片一样,编造《“情妇”举报副区长、公安分局长》帖文发布到网上,称其“贪污受贿20多亿、拥有60多处房产、包养10多名情妇,并杀害企业家黄某”。该谣言迅速被境内外网站、微博大量转载、评论,网民点击量逾千万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第四,打着所谓“披露历史真相”的幌子,或赞扬历史上作为中共政治对手出现的势力,如极力美化其他党派,或抹黑那些中共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及被树立为先进典型的人物,如雷锋。这些谣言在网上倍受青睐,部分网民以此当做解构权威、反对特权的幌子,使之成为在微博上吸引粉丝的大旗。这类谣言尤其值得关注和警惕,因为其特有的政治色彩,在微博上撕裂正统观念,造成左右对立,产生极坏的社会影响,消解社会正能量,威胁执政党的群众基础。
三、主流媒体破除“谣言法则”的策略
第一,针对“塔西佗陷阱”中的对抗式解读受众,应调整报道角度和报道语态,利用新媒体通道和平台辟谣
根据霍尔的的理论,编码位于传播者一端,是指将信息转化成便于媒介载送或受众接受的符号或代码。译码位于受传者一端,指的是将接收到的符号或代码还原为传播者所传达的那种信息或意义。新闻报道是记者、编辑或编导、主持人进行新闻采写、报道的一种编码,作为编码员,而受众是对新闻进行理解、解读、诠释的解码者,受众因受教育程度、外在环境、既有经验等方面的影响,解读方式,也千差万别。霍尔曾依据接受者译码符合文本含义轴的程度,将译码分为投合性译码、协调性译码、背离性译码等三类,投合性译码指接受者的理解与传播者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一致的;协调性译码指接受者的译码部分符合传播者的本义、部分违背其本义,但并未过分;背离性译码则接受者所得意义与传播者的本义截然相反。
对抗式解读的受众则是背离性译码者,也常常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他们通常在政治类等事件中因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对主流媒体的信息进行普遍的、彻底的对抗性解读,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特别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利益冲突表现的尤其突出,受众对传统媒体对抗性解读多发的领域,正是公权力越轨最多的领域,这种越轨或者表现为权力的滥用,或者表现为权力行使的消极。”
在主流媒体进行“辟谣”时,以上三种受众同样存在,因而要有针对性的调整传播策略,要保持并继续赢得协调性译码者的支持和信任,使其感染协调性译码者。而对于背离性译码者,则要重点施力,做到“逐个击破”。
作为编码者,要体察新媒体时代的受众心理,他们对新闻品质要求更高,对新闻报道的话语和姿态有了新的要求,如枯燥的语言、口号式的宣传、空洞的报道都感到厌烦,甚至专家的解释都成为他们段子炒作的素材。以此在辟谣时,更应顺应新媒体的话语特征,在传播姿态上,也要贴近受众, 使其感到被尊重,知晓权得到保障。既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又彰显传媒的公信力和亲和力。
另外还应利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用网络语言和社交方式推送辟谣信息,并拓宽传播形式做好网络舆情引导与疏导工作。如人民日报的《求证》栏目、新华社的《中国网事》、央视网的《辟谣联播》成为“谣言粉碎机”,日渐赢得公众信任。如《中国网事》专设“网事求是” 板块,从2012年12月20日至2014年2月27日,已辟谣或澄清类新闻近700条,围绕网上热炒或社会热议、民众关注的话题进行回顾并用红色标示找出关键点,或一一剖析谣言漏洞如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伎俩,或亲自调查取证让谣言无处遁形。“网传城管执法逼女摊贩跳河为不实”“网传北大校长周其凤艳照为不实” “铁道部称网传高铁辐射严重为不实”,有效遏制了在网络疯转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不实信息。
第二,力求信息平衡,切断谣言引爆点
谣言的根源在于信息失衡,尤其是在矛盾多元的社会中,信息失衡更是导致谣言四起甚至引发危机的一大源头。传谣者和造谣者通常认为自己处于信息弱势方,期望获得更多的信息以满足减少焦虑、威胁,而他们通常认为在传播强势方控制信息流通,他们想通过传播便捷的有限信息,哪怕是不确定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突破强势方的控制,从而做出解读和判断,以此寻求自我保护。
主流媒体应以此为鉴,在谣言出现苗头,尤其是谣言偏好性话题出现时,及时与政府或企业的相关部门沟通,第一时间释放信息,使得信息传播客体产生心理的满足,营造一个信息平衡的同时也切断了谣言的生长时机和落脚点。公开、正面、公正的应对谣言,填补受众与媒体间主观想象出的信息差,这无疑是切断谣言引爆点的有效途径,如在2014年3月1日的“昆明暴力袭击”案件中,对于除昆明火车站之外也发生类似事件的谣言在短时间内借助主流媒体进行辟谣,并在央视等主流媒体反复、滚动播出,减少了民众的恐慌情绪。人民日报微博也连续辟谣,分别以“辟谣!成都武侯区未发生少数民族口音人员砍人警情”“昆明暴恐案后,这些都是谣言!”等为题粉碎因恐怖袭击产生的谣言。
第三,主流媒体应当成为谣言的“检测仪”“定位仪”和“导航仪”
在拉斯韦尔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将环境监视(surveillance)视作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 。主流媒体更应在谣言出现时明辨是非真伪,剖析机理成因,对于深层次问题要心若明镜,不被情绪、偏见裹挟,甚至沦为推手。主流媒体暗含理性、权威的特性,应在审稿发稿时更加谨慎,不信谣、不传谣是基本底线,在此基础上更要勇于辟谣、敢于批谣。美国媒体也在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陷入了“未证实,先报道”的恶性循环中,透支了主流媒体公信力。美联社重新修订了自律规范,明确了信息来源核定制度,如严格要求员工在使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作为报道对象之前,必须事先联系当事人本人,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信息的真实性后方能发布,否则不允许随意转发。这不得不说是美联社在新媒体来袭时,为明辨真伪作出的应时自律。主流媒体做好定位仪和导航仪,普利策曾将媒体比喻为海上航行轮船上的瞭望塔,当它发现前方的冰山、暗礁时,能够及时向人们发出警报。在众说纷纭、人心惶惶之际敢于站出来推动和配合相关方面及时提供真实、客观、权威的信息。尤其是突发事件发生的危机时,恐慌情绪容易传染,急需确定的可以安抚人心的信息,媒体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权威信息跑在谣言兴起前,赢得主动权,焦虑是谣言产生的情绪机理,因而从根本上杜绝谣言滋生和繁衍。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王欢、祝阳,《微博时代反腐败类谣言的治理策略研究》,现代情报,2013年7月,第8页
卡斯·R·桑斯坦,《谣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王二平,《让谣言止于透明》,《生命时报》,2013年07月19日,第 10 版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王二平,《让谣言止于透明》,《生命时报》,2013年07月19日,第 10 版
赵卓,《网络推手“立二拆四”的终结》,《北京青年报》,2013年08月26日
吕尚彬,《基础传播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第164页
孙永兴,《论我国受众对主流媒体的对抗性解读》,《中国报业》,2013. 02(下) 第101页
周鸿铎主编,《传播学教程》,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7,第2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