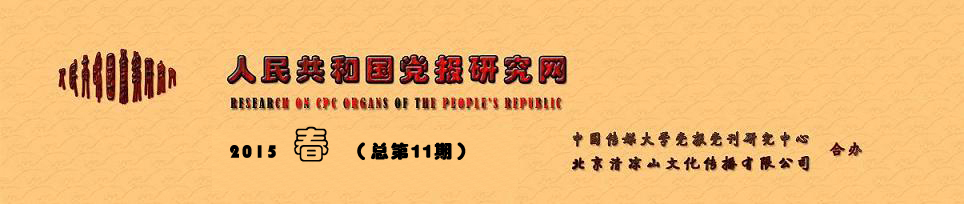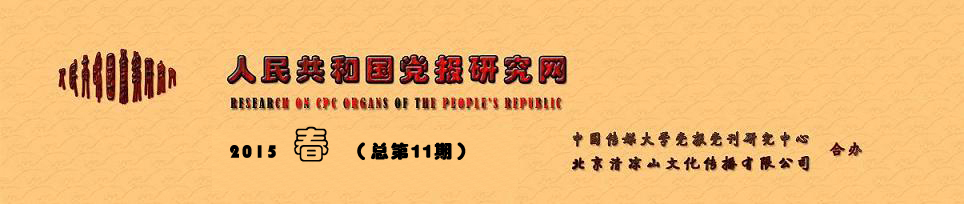我想就媒体融合中党报的版权问题谈点想法。恰好笔者最近参与或了解到的几件事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不妨一提。
今年全国政协组织新闻出版界委员考察新老媒体的融合问题,主要在党报、党刊、党台中进行。我发现,已经在尽全力投入媒体融合工作的传统媒体负责人,特别是党报、党台的同志不约而同地诉说,就是版权保护的困境问题:自己几百人经过艰辛采写和精加工的若干深度报道,还没有等到自己使用,或者刚刚使用,“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互联网媒体的若干门户网站“捷足先登”,“掠尽春光”。等到自己粉墨登场之时,已经铸就了“昨日黄花”的命运。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当新型媒体问世的时候,诸多传统媒体竟然缺乏分析判断,盲目拱手相让,甚至把新媒体对免费午餐的无偿享用,看作是一种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它居然那么“识货”,看中了我们的优质产品。等到今天明白过来事情的严重后果,只好叫苦不迭,悔之当初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在帮助阅读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同志《口述出版史》的书稿时,他讲到了当年制定著作权法,特别修改著作权法时的一些情形,很有咀嚼的味道。当年为了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有关内容写进著作权法,即使是人大代表,也是颇费心力,众说不一,甚至有尖锐的意见对立。宋老认为在我们国家,重物质财产、轻知识财产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习惯于对物质财产的承认,还不习惯于对知识财产的承认,好像只有知识才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最近的要算是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现全国人大教科文委主任柳斌杰同志的经典说法了:“过去传统媒体的新闻作品网站拿来免费使用,这是不正常的。”“花这么多钱,你还未用呢?互联网就先占用了,增加了它的点击率,提高了它的广告收入,这不符合新闻生产的规律。”“你们互联网,光喝免费牛奶,奶牛谁来养?”这是柳署长一句不无点穴的调侃式诘问。
从前不久举办的第七届版权年会论坛的几篇关于新媒体与版权保护的文章来看,我们的几位著名新媒体的掌门人倒是对版权保护有着厚重的实践体验,同时也有着鲜明的深刻见解。你看,盛大文学不仅紧紧地抓住了版权这个命门,而且对版权价值的最大化孜孜以求,从而站在了文化产品“食物链”的最顶端。他们毫不含糊,毋须暖昧地一语道破天机:版权即资产,而资产是需要精心呵护的。优酷土豆呢?建立了“合一而为”的多屏文化娱乐生态系统,为版权合作的规模化而努力,形成了依靠知识产权,创造收入多元化的盈利模式。爱奇艺的CEO和国航一位领导的聊天,颇具震撼力:他说你看我的一架波音737相当于一个中型国企的净资产,爱奇艺CEO说:你看我一个月播两部电视剧,其价值相当于一架737.你的737不会轻易被别人盗取,而我的版权瞬间就可被人盗取,等等。
版权问题就这样不以人的意志地被时代和社会凸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凸现在我们共和国党报人的面前,怎么办呢?思路倒不难寻觅,但做起来却是何等地艰辛呀!就思路讲,我们对自己所有的新闻产品都应有着强烈的版权保护意识,哪怕有点矫枉过正也不必担心,要紧的是让这种观念扎下根来,成为公理,成为常识,成为习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其中就包含了以著作权法治国、治业的要素。我们的新老媒体人,特别是传统的党报媒体人再不能对新闻版权的问题徘徊犹豫了。赶紧要在版权保护问题上下大决心了,甚至应向前追溯,寻求失去的版权利益,不要怕打官司,不仅不要怕,还要学会打官司,同时,我们还要在全社会为版权保护呼风唤雨,推波助澜。
其次,每家党报、党台单位应对自己的版权保护要有设计、有规划、有机构、有人员、有章法、有督查,成立常设部门,成为常规行动,进入永久系列。特别是对自己的版权产品应有一番认真的评估认定,即所谓的清产核资吧。要对自己版权家底有一本帐,究竟它有多大的盘子,可以带来多大的收益,实际上的收益有多少,流失了多少,流失到哪儿去了。在此基础上,争取对它的保护和增值。总之把属于自己的版权财产之保护发挥到极致。
再以从党国和政府方面讲,也大有文章可做。从立法角度看,很有必要予以补充加强:新闻产品不是有无版权的问题,而是如何使其获得应有的保护和实现。如果著作权法修改一时还不能到位的话,那么降格以求,先以国务院的法规来解决未尝不可。而且举一反三,不只是版权保护,包括以上相关连的若干问题都可以涉及。比如我们出版物的价格至今与价值极不吻合、且严重倒挂,就值得重视。
总之,为了应对全世界的互联网潮流,我们必须走融合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融合主要就是对党报、党刊而言的;为了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知识财产,而这其中版权是一个焦点,我们没有理由不把版权的事情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