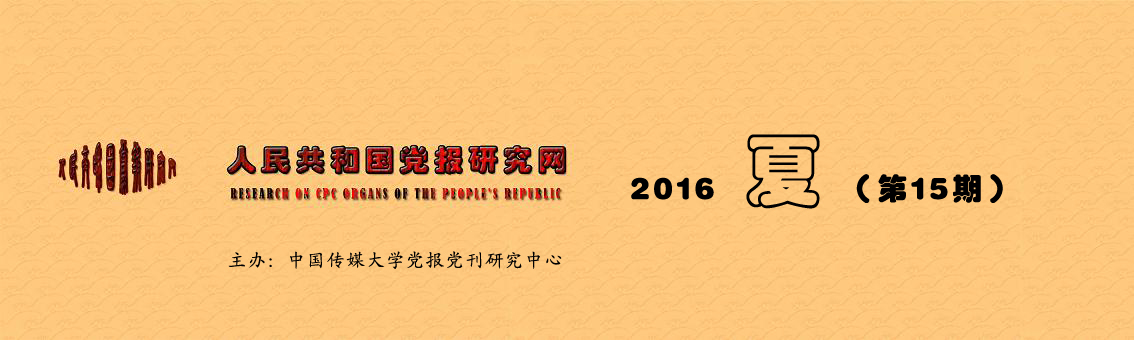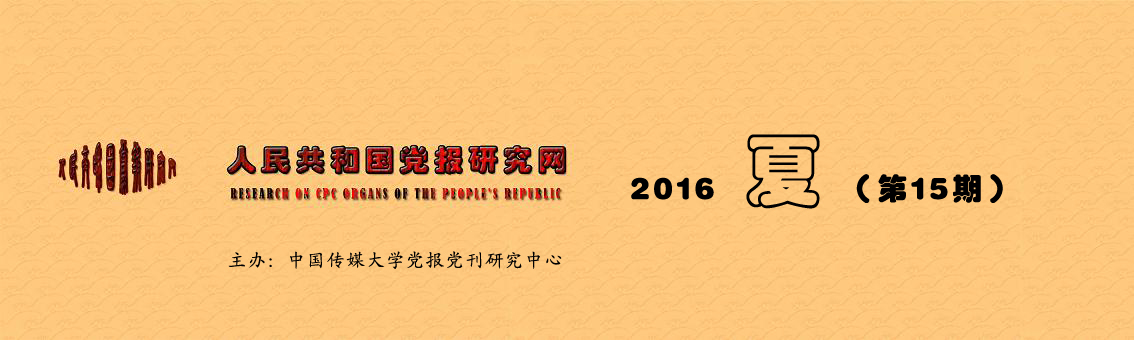评论难在立意,而立意贵在“站得高”。
“站得高”不是居高临下的训导,不是大而无当的空论,而是一种拨雾见天的透彻,一种准确清醒的判断,一种峰回路转的开悟,一种高屋建瓴的预言。诸葛亮有一篇《隆中对》,对魏蜀昊三国的力量消长以及历史演变进程,看得了了分明。在对形势作出正确分析的基础上,他制定了建立根据地、联吴抗曹的战略,挽救了刘备集团。这段史话,这篇短评,可为“站得高”的一个佳证。
人们向往“登高望远”,因为很多复杂的事情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因而人们总是在努力突破某种局限性,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现实,以便做出正确的抉择。辛弃疾说:“臣抑闻古之善觇(chan)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志。”觇国,就是观察和分析社会运动的规律,做到“知其受病”“逆其必殒”。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站得高”,望得远,想得深。
评论未必一定都要“觇国”,但无论题目大小,恐怕都需要站得高一点。这并不是要求所有文章能够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论人所未论,但至少说明,观察和分析问题没有高度,就很难给人有益的思想启发。
笔者推荐一篇立意较高的文章。
【例文】 题目:外媒可以无良,我们不能无脑(作者 樊征远 人人网2014年3月2日)
昆明出了惨案。29条鲜活的生命,在瞬间以最残忍的方式被剥夺。143名伤者在血泊中挣扎。他们的身后,是痛不欲生的亲人和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今天在新闻上看到,震惊之至,痛心之至。
查了下美国几大媒体对此的报道。很暧昧。我对他们的评价两个字:无良。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对惨案本身的描述并不多,相当大的篇幅用来有意无意地影射中国所谓的内部矛盾。恐怖主义一词,每次出现,一定要指明是新华社如此定性。CNN甚至给恐怖主义一词加了引号。一年前在波士顿马拉松案的报道中,对死者的哀悼,对伤者的生命关怀,对家属的慰问,对行凶者的谴责,此刻所剩无几。
所以波士顿的枪击中死了无辜平民,叫恐怖袭击;昆明死了无辜的平民,定性为恐怖袭击还要如此语焉不详?
意料之中。但我依然很愤怒。
美国政府与主流媒体终日高举人权与民主的大旗,而真正制定国家战略与政策时,何时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先?在美国的近三年时间让我逐渐明白了,美国的政府与主流媒体批评你,有可能说得对,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他们绝不是为了你好。你可以认同他们的某些观点,但你首先必须要明白他们的出发点。
在“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零和博弈心态泛滥的今天,美国媒体摆出这样暧昧不清的姿态,我不意外;但当我看到某些中国人也以和美媒类似的口气、大谈特谈所谓“真相”、所谓“原因”、和所谓“宽恕”时,我很震惊。震惊之余是痛心。
不知是中了圈套,还是别有用心。
此事的性质再清楚不过:恐怖活动永远是恐怖活动。人人得而诛之。残害无辜找不到任何借口。
有人也许会很委屈:我并没有故意为恐怖活动洗白啊。我只是在独立思考中提示大家深入分析。而且,我至少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不错。但是,言论自由不是颠倒黑白,原则问题不能混淆是非。理性的思考,必须建立在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深入的分析,不能模糊对灭绝人伦的暴徒最明确的批判。个人认为,现在是应该众志成城、旗帜鲜明地谴责恐怖行径的时候了。
老米按:这是一篇网络评论,主要是揭露西媒的虚伪和阴险。此类题材的评论不少,但此篇在立意上高人一筹。
第一层,外媒无良。作者抓住美国主要媒体对昆明暴恐惨案的歪曲报道,指明美国媒体故意把暴恐性质的问题处理成民族纠纷,其不良居心,显而易见。
第二层,不能无脑。这是最点睛之笔。西媒用报道挖坑,诱骗人们往舆论的火坑里跳。作者直言道出,西媒体貌似客观,实则蓄意挑动,我们必须警惕。
从评论的立意上说,人们会想到第一层意思,写出来也不难,而真正有价值的其实是第二层意思,此篇要义恰在于此。
一语点醒梦中人!
“站得高”,从客观上说,与我们所处的位置有关。在京广中心上俯瞰和在胡同里溜达,我们对北京的感觉是很不相同的。正如在人民日报工作,因为关注和研究的通常是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中央的精神知道得较快较准较全,自然应该在观察问题方面有某种优势。但这也不是绝对的。现在信息发达,上天入地,无远弗届,仅仅靠位置高度是不够的。“站得高”至少需要三个支点,曰历史眼光,曰广阔视野,曰辩证思维。
古人说,“以史为镜”,“以史为师”。史之所以为镜为师,是因为回望百年,思接千载,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历史所揭示的规律,而这正是把握今天、规划未来的重要依据。往小处说,阅历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遇到小小的挫折也许就会绝望,但对一个有经验的长者来说则可以泰然处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懂得挫折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历史是一部资政通鉴。管仲谈乱说治,有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汉武帝谈兴说亡,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而危。”这些俯拾即是的精辟之见都是历史经验。“站得高”首先是一种历史意识,懂得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不是说评沦作者必须是历史学家,而是说观察和分析具体有无历史的纵深度,分里是不一样的。
“站得高”,还有个空间概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笔下始有奇气。”所奇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见多识广,目光开阔。见得多,听得多,读得多,就能够建立起比较宏大比较科学的评价体系,考虑问题就能比较周全,洞悉本质,抓住要害。有些事情从一个局部来看,可能不无道理,但放到全局来看,也许另有一番道理。所谓“谋大局而无偏端”就是这个意思。
所有的信息和材料需借助于科学的方法加以处理才能变成有价值的思想。“站得高”就是能够掌握和运用科学方法,对事实和思想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处理。能够直观而准确地描述客观世界是一重境界,而能看到客观世界的变化并对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又是一重境界。大与小,强与弱,短与长,治与乱,战与和,胜与败等等,本来就处干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明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而要做到这一点非“站得高”而不能。
许多年前,和一位长者讨论国家兴衰问题时,他说过一句话,“钟鼓楼的家雀,见过大动静!”话俗理不糙,细想想,实在是高。
所谓文章立意,大约也是如此。
【例文】 题目:“埃及之春”为何成“埃及之冬”(作者 张维为 2014年2月20日环球时报)
2011年3月埃及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三个月后,我和美籍日裔学者、《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先生在上海就中国模式有过一场辩论。他提到了中国也可能爆发类似的革命,我说不会。我当时说:“至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体现出的,好像是人们要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4次,20年前它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失业,能不造反吗?我的结论是: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问题。现在叫‘中东之春’,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之冬’。”三年过去了,我当时的预测是准确的:“埃及之春”已变成“埃及之冬”,“阿拉伯之春”也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4次访问了埃及。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访问埃及的印象,这个词就是“爆炸”,特别是开罗,给人感觉是嘈杂(世界上分贝最高的城市)、拥挤(到处车挨车人挤人)、脏乱(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从来没人打扫过)。近十年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政治化,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便会燃烧爆炸。突尼斯的动乱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这场革命。
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来看,阿拉伯国家,只要真正搞普选,上台的一定是伊斯兰势力,而不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势力。果然,2012年5月的大选,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随之,埃及就陷入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持续抗争。2013年7月,军队罢免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这又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持续动荡。埃及似乎已经陷入了发展中国家植入西方民主模式后的那种典型的恶性循环:普选产生了民粹主义领袖,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埃及的危机说明了什么?首先,国家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也非常之慢,这种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其次,埃及的问题不是西方说的“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对于埃及面临的棘手问题,如人口爆炸,贫困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西方民主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而只会使问题恶化,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失序甚至崩溃。第三、它说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社会共识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在这个基础上推动符合本国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而是把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一揽子寄托于西方民主模式,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老米按:这篇节选的评论,具有预言性,又有现实依据,揭示了西方在阿拉伯地区鼓动“革命”,给这一地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可谓“站得高、看得远”一例。这也许这正是西方想做的事情,抑或是连西方也想不到的结局。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可悲也夫,可痛也夫!
作者之所以对埃及乱局有深刻分析,可能源于三个原因:一,四到埃及的经历;二,年龄之故,经历过太多的事情;三,由此而积累的巨量的比较和鉴别参数。
当然,最重要的是,作者能够切埃及动乱之脉,断西方颠覆战略之因,明中国稳步发展之理。精明老道,是谓“觇国”之策论也。